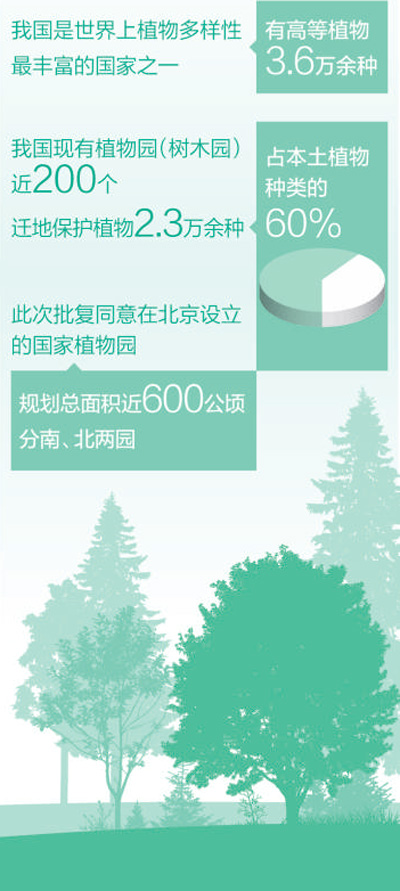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繁花:批注本》,我在朋友圈发了个Thanks note。金老师看到后微信我:“哈哈哈,总之这形式太复古……”自嗨自嘲溢于言表,却在我脑际萦绕。当然“复古”指批注这一传统“形式”,包括书的排版制作的“形式”也富有“复古”意味,然觉得不那么简单。打开此书标题页上:“《批注本繁花》:金宇澄著、沈宏非批注、姜庆共排版”。这是个集体工程,以《繁花》为主体,那么“总之这形式太复古”,是三位一体的。关于这部小说已经说得很多,但说它“复古”则新颖烧脑,且出自作者之口?或许早已有“复古”的念想,藉批注和排版而体现之?还是由于批注和排版而产生了新的认知?
对于这“形式的复古”,我没有深问,却在阅读批注本时多长了一份心眼,以下谈点体会。因为自己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自然会涉及一些相关的话题,不免专业的盲见和偏见。
自唐宋以来文学“复古”运动屡见不鲜,皆旨在“文以载道”,以上古三代“圣人之治”的乌托邦为号召。对现状不满而加以批判,合理合法,但强烈的道德理想反而压制了文学的创造。至明代中期,李梦阳等“前七子”打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号,以“形式”为核心,把某些古代文学风格与美学理想作为追求对象,就跟复古道统划清了界限。由于他们的作品带有摹仿痕迹,在创作上显得幼稚,然而“形式的复古”使文学回归其自身,走向创新的多样之途。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接下来是晚明时代。如所周知,李卓吾的“童心说”一呼百应,认为文学源自人的自然之性,顺从人性要求的发展,于是把四书五经视作糟粕,称《西厢》《水浒》为“至文”,刮起文学解放的狂飙。或可说李梦阳是晚明文学的先驱,如他宣言“真诗在民间”,已先声夺人。或可说人性即形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的欲望要求新的表达形式,其生命里有赖于欲望表达的持续可能性。
中国古代向来有对儒家经典与史籍的诠释传统,对小说作“评点”始于晚明万历时期。由于小说出版繁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金瓶梅》的“四大奇书”出现,为满足大众阅读与理解的需要,小说批注应运而生,李卓吾为《水浒》作评点,将理论付诸实践,即为存世最早批注的代表作品之一。《繁花》批注本中沈宏非在《上帝不响,像一切由我作主》一文中指出小说批注有“活批”与“死批”的区别:
所谓“活批”,即李卓吾、张竹坡、毛宗岗一脉,以“金批”为典范。将风中凌乱的说散本一把搇牢,于门户洞开的方块字平台上,大刀阔斧,榜掠备至;或订正bug,或径直刊落,敲金振玉,杀伐果断。借他人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直抒胸臆,生龙活虎,生猛到上头。
一顿操作猛如虎,晚明大批判,批活了词话金瓶梅,并且在百年之后,终于批出了一部从回目结构、人物主次到叙事脉络“一家人齐齐整整”的石头记。石头缝里,脂砚斋以“死批”一骑绝尘,其摆话之决绝,剧透之煞根,一句顶一万句。
何为“死批”“活批”?的确,任何批注必须以原作为圭臬,若奉原作为圣旨,不敢越雷池一步,即成“死批”;如果既忠于作者原意,又充分做到主观能动,无论“大刀阔斧,榜掠备至”或“直抒胸臆,生龙活虎”,乃形容一种绝地而生的创新境界,给“批注”注入真性情,自铸伟藻丽句而独具风格。称“金批”为“典范”,更指金圣叹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他把《西厢》《水浒》与《庄子》《史记》等同列为“才子书”,因此“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扶正了小说的正房地位,奠定了汉语小说作为‘门类’的独立性,也为日后与西式小说的对标,布妥了适配的接口”。
这段极具风格化的文字表述历数文学史上小说“批注”的家门,从四大奇书到《红楼梦》,名家辈出,追溯源流如数家珍,当然也自居于传统之列,以继往开来为己任。此中我认为已含有“复古”的意蕴,且用“死批”和“活批”来理解很有意思。文学经典绝非一成不变,其生命在于流动与更新,如果持一种本质主义的“死批”态度,就会导致其死亡。反之“活批”即救亡,复古即顺今求变,用生命点燃过去的灰烬,唤醒幽灵,在裂变中走向新生。
沈文说:“以白描见长的《繁花》,却有一种把现代汉语小说‘倒退’到话本的返祖倾向。批注者,无非就着这种倾向顺坡下驴,做些勾搭、挑唆、起哄之勾当。”这一句非同小可,所谓“倒退”“返祖”,在在道出其“复古”倾向,而批注为之推波助澜。事实上金宇澄在《跋》中宣称:“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且表明其尊奉“话本”为小说正宗,《繁花》即心追步摹之作。他说:“《繁花》感兴趣的是,当下的小说形态,与旧文本的夹层,会是什么。”又说:“话本的样式,一条旧辙,今日之轮滑落进去,仍旧顺达,新异。”力图使“小说形态”回归“话本”传统,在“旧文本的夹层”中探索“顺达,新异”之变,也即“复古”之真意。
本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是《繁花》的卷头题词,凸显“作者”主体,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概,蕴含自我作古的慷慨雄心。就“不响”这一独家修辞而言,于有无之间顿生波澜,纵贯小说不计其数。沈宏非却以此为题,首先声称“作者已死”,据此声辩“死批”与“活批”之别,由是一刮两响,置换主体,以“批者”俨然自居文本饕餮之C位,这一出逼宫戏码,不可不谓之牛!所谓“作者已死”出自福柯与罗兰·巴特,将“作者”看作符号,是解码编码的文本生产之物,与作者的真身无干。虽是恶名昭彰的后现代标签之一,却一举击破从来对文学经典本质主义的迷思,昭示在文本面前一律平等,将经典的流动与意义交给读者,即使引车卖浆之流也有其解读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沈批一面宣称“作者已死”,一面吊诡表明:“批注者周旋于《繁花》丛中,每遇绝妙好词,纳头便拜;逡巡于《繁花》之广筵长席,或择适口者冷不丁也伸一筷子,把人家流水席吃成一个人的自助餐。”就像“端个茶、递个水、摇个旗、呐个喊,也不忘暗中使个绊子,戳把轮胎”。这颇似巴特的做派,一面沉醉经典的魅力之中,欲仙欲死,一面鼓吹批评的天才,施展点石成金的魔力,使批评文本不下于原作,同样臻至美的境界。
的确,纵观这本《繁花》的批注,尽管“等于说书先生搞外插花,罡头开花”,却踵事增华,异彩熠熠;满纸烟霞,机锋四伏。对于批注,我这里做不到剧透——力不逮也。《繁花》共31章,前置“引子”,沈批曰:“如果《繁花》是痴男怨女的一帖药,此段便是药引子。”对这部分的批注为全书提供样本,似可以“体例”视之。
过去统称小说“评点”,“评”是批评,“点”是“圈点”。(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8)改称“批注”,涉及排版形式的重大变更,对于复古新变来说具标志性。批注分两种形式,一种是紧跟文本之后的词语解释,所释词语下标横线,用枣红色楷体字排印注文。如在“娘希匹”后注“宁波粗口”。也不尽是词语解释,如在“梅瑞双颊一红”后注“红得蹊跷”,具评论性质。另一种是在所释词语下标圈点,在旁边辟一灰色方块,用枣红楷书直排注文,字数较长,除解释词语出处之外,附以评论。另外在每章之末有一段批语,对内容做一番利于鉴赏的提点。
批注展示广袤视野与深邃知库,囊括寰宇,笼罩三才,其释词之精详、疏通文理之精微,令笔者击节叹赏,然难言其涯涘。若用时下的人文“跨界”的时髦说法,如用北方话解释上海话,用日本卡通《蜡笔小新》解释“美女”取代“小姐”的使用,或谓某皮鞋款式见诸某好莱坞女星等等,在人文领域中自由穿梭,打通中西、文史、图文及文艺类型之间的隔阂,所谓五湖四海一家亲,显示出海纳百川的“海派”风貌。
我想着重指出沈批的当代性,这对于“形式的复古”至关重要。关于批注方法,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提出“古典”与“今典”的诠释原则。前者指对历史典故的解释,即一般引用现存典籍的考释方法,而“今典”则指涉当代史。如通过钱谦益与柳如是之间诗文与同代人的书写材料来探寻两人之间感情发展的细节,并还原当时的政治事件与朋友圈交往等,遂展示明清之交天崩地裂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在古典方面,沈批对于“萌蘖”一词引用《孟子·告子上》的文本(页245),或在解释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哀感顽艳”一词时,注曰:“典出三国繁钦《与魏文帝笺》,收入《文选》卷四十、《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页182),如此追本溯源,大有清代考据家路数。然而沈批对于《繁花》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今典”的挖掘,当然——也是最难的部分。
本来《繁花》就是一轴《清明上河图》式风俗画卷,生动再现“话本”传统的当代活力。围绕沪生、阿宝和小毛及其亲友描绘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全方位扫描其物质与心灵世界,不厌其详地铺陈城市景观与日常生活物件的细节,如小说的插图所示,七十年代的沪西工厂、四十年里卢湾区的路名或某街角的变迁以及各式各样民间自制的不锈钢开瓶器等。金宇澄声称用“画笔替代伟大的相机镜头,记录”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城市。
金宇澄手绘的《繁花》插图。画笔代替伟大的相机镜头,记录了瑞金路长乐路这个街角四十年的戏剧性变迁。
沈批亦步亦趋,对百科全书般浩瀚词语一一作注,不放过一条路名、一个人名、一座商厦、一种品牌……打捞记忆,如对历史遗迹的考古作业,为原作增添了无量文本,不限时空与各种文献相联系,结果是将原作历史化,织入文化网络,蕴含种种物质和情感的微观文化史。一个例子是第六章里梅瑞处理她母亲去香港之后留下的衣饰等物,对于服装面料、皮鞋和旗袍的款式,包括对钮扣款式的描写占了三四页(页133-136)。对这些衣饰的浓描细写不仅勾勒出梅妈的大半人生,也刻意记录市民的物质记忆,而在沈批那里,哪怕是“滚边包纽、暗纽、挖镶、盘香纽”之类,也说得津津有味,平添了无数信息,使这段叙事读似微型时尚文化史。
批注加强了《繁花》的历史性,而更大挑战则来自文学性,需在疏通阐释原作文脉文心之际体现批者的文学风格,也是一趟探索自我的文学之旅。上述对梅妈衣饰的叙事,实际上全是梅瑞在电话里说给康总听的,“康总不响,心里开始烦”,批注说:“批者已经烦很久了。”正是从受众角度批注在这长段叙事中不断点出梅瑞与康总之间的心理战,如“这一回合,康总赢”“转守为攻”“见好就收”等,帮助读者理解小说对人物的刻画与艺术表现手法。有意思的是,最后梅瑞说:“反正,这个房间里,妈妈是一样不想再看见了,完全可以结束了。”沈批曰:“多种面料,款款衣裳,交代了梅妈的半生。康总若熟读张爱玲,电话里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之叹,此其时也。”(页137)这里向张迷抛了个媚眼,其实在《繁花》开头对“平安电影院”的批注就引了张爱玲的话。
运用文学文本作笺注,最能、最有趣体现了批注的文学性与批评个性。引用张爱玲是一个借光、借声动作,而引征古今中外的作品,使《繁花》成为众星献声、假声炫技的舞台,交织着作者、批者与读者的众声喧哗。这种全球性奇观,远非金圣叹、脂砚斋所能梦想。所引作者鲁迅、茅盾、肖洛霍夫、卡尔维诺、普鲁斯特、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等,不仅显示批者的阅读兴趣与素养,更传递一种文学理念,展示经典作品与世界文学流通与对话的必然潜能。
批注常引用晚明文学,如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解释“紮火囤”(页243),以陈继儒《小窗幽记》解释“泉下骷髅,梦中蝴蝶”(页131)等。更值得注意的,在用袁宏道《觞政》解释“狂花病叶”时说:“《繁花》里的男女老少,人人都是公安派铁粉,金句张嘴就来。”(页493)批者自己对晚明文学情有独钟,也基于对《繁花》的心有灵犀的理解,可见他们心目中晚明文学的特殊地位。的确,沈批中金句频频,字里行间不胜枚举,如第十五章里描写5室阿姨与黄毛在车床的轰隆声中成其好事,批语曰:“每写男女苟且,不是田间地头,就是村前村后,如此重金属工业风现场实属罕见”,并以“工业立体主义画风”(页291-294)形容其艺术创新特点。另如第十一章里,姝华走过瑞金路长乐路街角,看到天主堂被拆毁,从阴沟里滚出人的眼珠,使她惊厥:“姝华微微发抖,勉强起身,慢慢走到淮海路口,靠了墙,安定几分钟。”批语曰:“从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到东野圭吾,从大正、昭和到平成,历代日本作家在‘临终之眼’(末期の目)上孜孜不倦的文学追求,全部到此下马。”(页229)同样举重若轻,仅寥寥数语点出《繁花》叙事之精妙绝伦,秒杀日本同行。
各章尾批皆用心结撰。第二十六章阿宝与李李在云南路一家羊肉店的对白,批注演绎临济佛法的“生龙活虎之姿”(页540),涉及中国传统思维与写作方法的精髓。最后一章尾批对于“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中“不响”的阐发(页669),包括对于“像”的暧昧意义的解释(页662),均是对批注宗旨的重要补充。如果晚明文学是文学个性的隐喻,那么沈的“狂批”(毛尖语)极富晚明小品的神韵而具多元杂拌的当代气息,无论是恣肆倜傥、潮语拧巴、斜杠风流……都给原作轮换风情万种的面具。
虽然,我不免吹毛求疵,觉得对个别词语上的解释有可斟酌处。如把“会乐里”释为“某青楼”(页242),过于简略,实指青楼集聚的弄堂名。(熊月之主编《上海大观:名人名事名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540)“十姊妹”(页263)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妓院中,当时杂志刊有“十姊妹”照片,孙漱石作小说《十姊妹》,与电影《红粉骷髅》有关。
马俊丰导演、温方伊编剧的话剧《繁花》近日又将在美琪大戏院上演。图为孙之鸿饰演的阿宝。
最后,却是绝对超前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将“排版师傅”与作者、批者同列,恐怕在世界出版史上也属首创。常见的是艺术类书籍标出设计家或艺术家之名;或者小说插图本标出画家之名,但排版一般被视为工艺性质,与艺术不能同日而语。在中国,艺术上的雅俗之别甚严,如《点石斋画报》采用西画透视法,对中国美术史影响深远,画师计有23人,但仅知其名,对最著名的吴友如也所知甚少,更遑论其他画师。今人论及当时画家必称任伯年、吴昌硕,而画师们却默默无闻,史家深以为憾。《繁花》批注本破除传统偏见,仅是个引子,更体现了一种技术与人文的新观念。简言之,与《繁花》的激活话本传统的“复古”思路如出一辙,对印刷技术的古今演变的历史作反思,对批注本排版采用一种新字体,重现古代雕版活字之美,成为一次完美的技术与人文的合作,在当下来自技术的紧迫挑战的境遇中提供一种人文突围的方式。
姜庆共在《做了一回“排版师傅”》一文中说:
旧气新意交错、玩味,是这次批注本排版所刻意要表现的版式细节。中文古书刊刻及活字排版,大都一字一格,字字见方,行文气息悠缓,阅读通畅。一百多年来,西式标点、白话文、横排和简体字的出现,渐渐影响到中文排版的格律。这次《繁花》批注本的正文排版,依然使用了文字和标点各占一格位置的“全角”方式,这是中文书籍排版自竖排转为横排后,仅剩的古意。(页681)
这里清楚表达了“形式的复古”的意思,出自一种倒拨时钟的奇怪构想,《繁花》需要一种能“符合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气质的正文字体”,结果采用一种稀见的“汉仪新人文宋”字体,“其笔画比上世纪的正文宋体字略粗,字形结构不同于传统,不循规蹈矩,带给人一种镌刻的手工感。这也是我一直在寻觅的略显复古的新字体风格。”这就是批注本所呈现的效果。同样封面也独一无二,看上去是清一色枣红,四周是出版信息的小字皆凹进页面,中间是“繁花”两个大字,其剪纸折叠字型让人想起近年来金老师的绘画艺术的现代风。整个设计简朴大方,含一种“含蓄”的传统诗学,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这不单是排版问题,而是在印刷历史的新旧断裂处实践一种技术上的革新,落实在每一个字的排版过程中,于是有了这本新的《繁花》,与原作、批注融为一体,体现了“形式的复古”的思想,从传统获取创新的契机。当然,这是在现有条件的限制下探索一种改良之途,尽管如壶中风暴,却气象万千,蕴含着革命性勇气与契机,其中“汉字”本身负载着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人文信念,与技术发展共进退,应对未来的危机与机遇。如姜老师最后表示:“尽管汉字复杂,但输入每款汉字的笔画字型特征后,实现AI造字的目标,应该也不远了吧。”(页682)与此相似,最近读到金宇澄《缓慢移动的梅花和料峭柳色》一文,最后一句:“这也是文字的好处,这样以字刊出,仿佛就出现了将来的美景。”(冷冰川主编《唯美》,商务印书馆,2022年,页14)他把文字比作一条缓缓行驶的船,悠然观赏河上风光,在文字的愿景中寄托着乡愁。
作者:陈建华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标签: